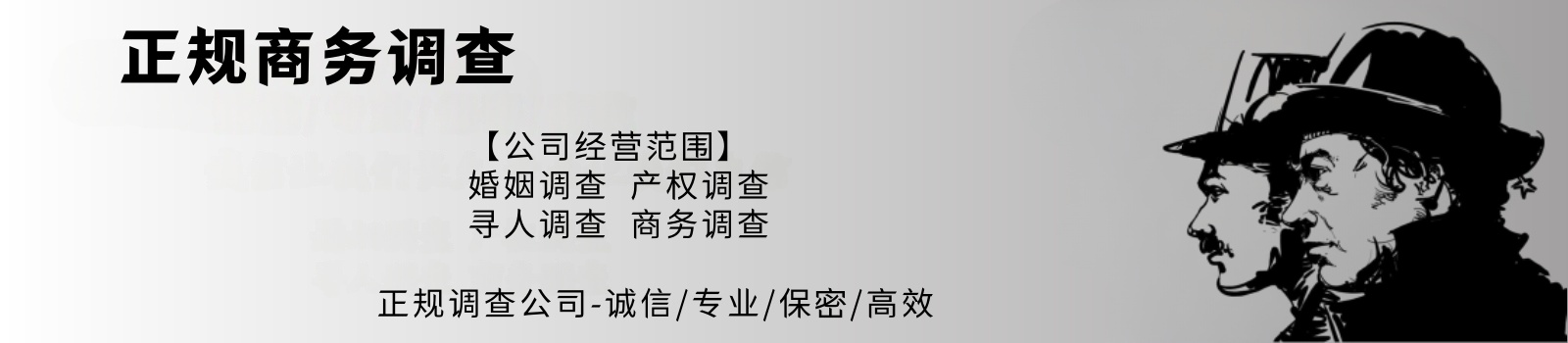- 手机:
- 13728687007
- 电话:
- 13728687007
- 邮箱:
- admin@youweb.com
- 地址:
- 广东省中山市
手机震动的时候,我正站在高铁站的落地玻璃前。
室外,南边那个季节的雨丝儿蛮密出轨的我,把远方的城市轮廓给搅和得看不清了,变成一片灰蒙蒙的水彩画。
屏幕亮起,不是丈夫陈宴的,而是一条来自铁路App的推送。
您关注的常用同行人“小安”已经登车,G1314次列车预计在18时30分到达本站。
小安。
我盯着那个备注,感觉胃里有块冰,缓慢而坚定地沉了下去。
这是我在陈宴手机上做的操作。他工作性质决定经常需要外出,担心他工作繁忙时忽略汇报事宜,所以我擅自将他身份证号码加入了我设置的“常用联系人”列表中。
他知道,并且笑着说我像个操心的老母亲。
可这个“小安”,是谁?
两天前,我还为他熬了一锅汤。
是猪肚鸡,加了党参和黄芪,小火慢炖了整整三个小时。
他说最近项目压力大,晚上总是睡不好,人也瘦了一圈。
我把汤盛出来,吹了又吹,才递到他嘴边。
“尝尝,我特地问了妈,她说这个最养胃。”
陈宴斜倚在沙发里,眼下隐约可见深色阴影,他抿了一口饮品,喉咙微微起伏,随即浮现出一种倦怠的笑容。
“好喝。辛苦了,阿清。”
他伸手过来,想揽我的肩膀,我下意识地避开了。
不是赌气,是算着日子。
今日已届排卵日之次日,医者曾告诫,须维持平和心态,切勿视此为负担。
结婚已经五年了,尝试生育也有三年时间了,起初充满希望,后来变得冷漠,现在更是如同例行公事,“淡定”这个词,比争取到一个价值千万的项目还要困难。
陈宴的手停在空中,过一会儿又若无其事地收了回来,拿起碗,一点一点,把里面的汤全都喝完了。
连汤里的枸杞都捞了起来。
他告知阿清,下周将再次前往邻近城市,参与一个新项目的启动会议,预计会持续三天时间。
我“嗯”了一声,去厨房洗碗。
水声潺潺不断中山哪里有正规小三侦探公司,我注视着池中漂动的油渍,猛然想到,我们的结合宛若这水潭,表面看似兴旺热闹,内里却淤积着诸多纠缠不清的污渍。
他母亲赠予的玉坠,现摆放在入门处的柜子上,据说是为了祈求平安,兼护子孙。
那块温润的白玉,如今看来,也像一块冰。
高铁站的广播响了。
G1314次列车,正在进站。
我保持不动,只是默默注视着那道亮白色的光,仿佛是一把锋利的工具,穿透了湿润的夜晚。
车门打开,人潮涌出。
我一眼就看见了陈宴。
他穿着我给他买的灰色大衣,身形挺拔,在人群里很显眼。
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孩。
那个姑娘披着一件雪白的羽织,盘起一条高高的发辫,她脸上洋溢着重逢初见的纯真和清透。
她仰着头,正对陈宴说着什么,眼睛亮晶晶的,像落满了星星。
陈宴低头听着,侧脸的线条柔和下来,是我许久未见过的松弛。
然后,他抬手,非常自然地,替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额发。
那个动作,亲昵,且熟练。
女孩的脸颊泛起一丝红晕,像初春的桃花。
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凉了。
没有想象中的歇斯底里,甚至没有眼泪。
我只是觉得冷,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带着湿气的冷。
我拿出手机,对着他们,平静地按下了快门。
照片中,明亮的照明,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亲近的样子,形成了一个非常明了的景象。
是证据。
我是一名合同律师,工作教会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凡事讲证据。
我收起手机,转身,汇入出站的人群,与他们背道而驰。
回到家,我没有开灯。
黑暗像一张巨大的网,将我包裹。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墙上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沉闷地跳动。
像是在为我死去的婚姻,倒数计时。
大约半小时后,门锁传来轻响。
陈宴回来了。
玄关的灯亮起,他看到坐在黑暗中的我,愣了一下。
“阿清?怎么不开灯?”
他朝这边走来,身上裹着户外的冷气,还有种淡淡的,不是我的香水气息。
是甜橙和白麝香的味道,年轻,又带点天真的诱惑。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只是抬起头,在昏暗的光线里,静静地看着他。
“回来了。”我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谈论天气。
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嗯,回来了。路上有点堵。”
他一边说,一边换鞋,试图用日常的琐碎来掩盖那份不自在。
我没有戳穿他。
我等着他走近,等着他像往常一样,俯身给我一个拥抱。
他果然这么做了。
但在他碰到我的前一秒,我把我的手机,放在了他面前的茶几上。
屏幕亮着,停留在相册界面。
那张在高铁站拍下的照片,清晰,刺眼。
陈宴的身体,瞬间僵住了。
他垂下头颅,凝视着那张影像,面容上的红润逐渐消散,最终只余下一片黯淡的苍白。
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能清晰地听到他骤然急促的呼吸声。
“阿清,你……”他的声音干涩沙哑,“你听我解释。”
“好。”
我只说了一个字。
接下来,我倚在沙发上,双手抱臂,做成了会议场合里最常见的一种架势。
一个等待对方陈述的,冷静的倾听者。
他的解释,混乱,且苍白。
“她叫安然,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很有灵气。”
“这次出差,她跟着我一起,做会议纪要。”
“我们……我们没什么,就是普通同事。”
“高铁站那个,是……是她头发乱了,我就是顺手……”
他说一句,我看他一眼。
我的视线毫无感觉,如同精密仪器,审视着他全部神情中的虚假掩饰。
他渐渐说不下去了。
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说谎者往往难以控制地提升说话的快慢,同时身体会做出一些不必要的动作。
比如,陈宴现在正反复摩挲着自己的手指。
我等他彻底沉默下来,才缓缓开口。
“陈宴,我们结婚五年。”
“你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合伙人,我是一家律所的合同律师。”
我们都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社会人士,需要懂得一个最核心的准则。
我顿了顿,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
忠贞,乃婚姻这份契约里,最关键的约定。它并非天赐的礼物,而是必须履行的责任。
他突然抬起了头,目光里充满了惊异,带着几分难堪,又夹杂着一缕因我的沉着而引发的烦躁。
“阿清,在你眼里,我们的婚姻就是一份合同吗?”
“那又如何?”我反诘,“一个以情义为纽带,以法规为后盾,明确了彼此责任与利益的持久盟约。此刻,你却背弃了它。”
我的言辞,犹如锋利的解剖工具,穿透了所有温情脉脉的外衣,显现了其中冷冰冰的交换本质。
他被我堵得说不出话来,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颓然地垂下头。
“对不起。”
这三个字,他说得极轻,像是怕惊扰了这死寂的空气。
“‘对不起’是态度问题,不是解决方案。”
我站起身,打开客厅的灯。
整个房间瞬间被白光笼罩,亮得有些刺眼。
“现在,我们需要谈谈解决方案。”
我给他倒了杯水。
然后,我把我的手机推到他面前。
“安然,对吗?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
陈宴的脸色更白了。
阿清,你,到底意欲何为?这桩事纯属我们私下解决,请你不要干预,她毕竟刚离开学校,是个涉世未深的新人。
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下意识地维护她。
我的心,又被细细密密的针扎了一下。
疼,但是不致命。
“陈宴,你搞错了一件事。”
我无意参与什么正宫驱逐偏房的场景,那样做既缺乏格调,又显得难堪。
我需要核实若干信息,以便衡量你违反约定的严重性,并且,要判定这份协议是终止,还是修订部分内容后继续执行。
我的冷静和理智,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陌生和恐惧。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看一个怪物。
“你……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取决于你们到了哪一步。”
我看着他的眼睛,平静地重复:“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
这一次,他没有再拒绝。
他颤抖着手,在我的手机上,输入了一串号码。
我当着他的面,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三声,被接起。
一个怯生生的,带着几分甜糯的声音传来。
“喂?陈工?”
我开了免提。
陈宴的身体猛地一颤,像被电击了一样。
“你好,安小姐。我不是陈宴,我是他的妻子,苏清。”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然后,是一个带着哭腔的,微弱的声音。
“……对不起。”
又是这三个字。
廉价,且毫无用处。
“安小姐,我现在不想听你的道歉。”
“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我家一趟。地址我会发给你。”
倘若你不出席,次日我们便到你工作场所,或你双亲眼前,当面处理这桩事务。
我说完,不等她回答,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不是在威胁她,我只是在陈述一个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把所有当事人聚集在一起,当面质证,一次性解决问题。
这是我处理商业纠纷时,最常用的方法。
陈宴瘫坐在沙发上,用一种近乎绝望的眼神看着我。
“阿清,你一定要这样吗?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
“绝?”
我笑了,但眼底没有一丝笑意。
陈宴,我这样做是为了保障我作为合法妻子的应有权利,这并非绝情,而是出于职业素养。
我未曾当街阻拦你们,也没去你们单位滋事,更没对你出言不逊。我给予了你,也给予了她,成年人应有的最后尊严。
“而这份体面,是我用我自己的教养和克制换来的。”
因此,请你停止扮演那个委屈的角色。这件事情中,唯一承受伤害的人,正是我。
安然来得很快。
她站在门口,脸色苍白,眼睛红肿,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她脱掉了那件白色的羽绒服,披上了一袭深色的衣裳,好像有意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我让她进来,给她倒了杯温水。
陈宴坐在单人沙发里,从她进门开始,就没敢抬头看她一眼。
客厅里,三个人,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对峙。
我打破了沉默。
安小姐,不用慌张,请放宽心。今天请你到这儿来,并不是要责罚你,只是想将事情原委调查明白。
我坐在他们对面的主位上,像一个法官。
“我问,你答。可以吗?”
安然捧着水杯,点了点头,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
“你和陈宴,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小声说:“……三个月前。”
“到哪一步了?”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插进了沉默的空气里。
安然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她求助似的看向陈宴。
陈宴依旧低着头,像一尊石雕。
我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等着。
沉默,有时候是最好的审讯工具。
过了很久,安然才用蚊子般的声音说:“……都……都有了。”
好。
事实清晰,证据确凿。
我点了点头,看向陈宴。
“你呢?有什么要补充或者反驳的吗?”
陈宴缓缓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却只说出两个字。
“……没有。”
他承认了。
我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虽然砸得我五脏六腑都疼。
“很好。”
我从茶几下拿出纸和笔,推到他们面前。
“既然事实清楚,那我们就来谈谈解决方案。”
“我有两个方案。”
“方案A,我们离婚。”
我说出“离婚”两个字的时候,陈宴的身体剧烈地抖了一下。
安然也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反应出轨的我,继续说下去。
依照婚姻法规,你属于有过错的一方,在解除婚姻关系时,我将要求你放弃全部财产。我们婚后形成的共有财物中山正规私家调查公司,诸如这处房产,两台汽车,还有你名下公司的股份,我会委托经验丰富的法律人士,为我争取到应有的最大比例。此外,我也会向你索要情感抚慰金。对此,你有不同意见吗?
陈宴的脸色,已经不能用苍白来形容了。
他目光落在我身上,神情中流露着惊慌,他清楚,凭借我的业务水平,一旦我说出口,就肯定能办成。
“方案B。”
我停顿了一下,给他们留出消化的时间。
“我们不离婚。”
不过,务必即刻与安小姐终止一切往来。职场上,我将安排她离开你的团队,甚至可以考虑解雇她。个人方面,所有通讯渠道都要屏蔽。你们俩,从此不再有任何接触。
“同时,我们需要签订一份婚内财产协议的补充条款。”
你的全部财产,涵盖工资卡与股权收益等,都由我负责处理。每月我会提供固定数额的生活费给你。
你的手机,微信,以及全部社交应用,我都有权随时检查,你的车辆,必须加装GPS定位设备。
第三点,也是核心要求。倘若再犯类似情形,你将丧失全部婚姻存续期间积累的财富,一无所有。同时,你必须签署一份悔过书,明确自己的错误,这份悔过书,我会呈送给双方的长辈,以及你的企业决策机构。
我每说一条,陈宴的脸色就更难看一分。
安然已经吓得哭了出来,小声地抽泣着。
我说完了。
整个客厅,只剩下她压抑的哭声。
我看着陈宴。
“两个方案,你自己选。”
“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
说完,我站起身,走进了书房,把空间留给了他们。
我没有关门,只是站在门边,看着窗外的雨。
雨下得更大了,敲打在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不是在给陈宴选择。
我是在给他,也是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一个把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最后的机会。
我知道他会选哪个。
他不敢离婚。
离开的后果,他难以负担,不仅涉及物质财富,更包括他费力维持的社会声望和被公众认可的正面形象。
而我,也不想离婚。
不是因为还爱他。
说实话,在那一刻,我不知道什么叫爱了。
我只是不甘心。
无法接受我五年的青春年华,我为了这个家倾注的无数心血,我为了怀上孩子而忍受的数百次针刺,最终,只得到一句无足轻重的道歉,以及一个什么都没留下的男人。
凭什么?
犯错的人,就该付出代价。
这才是成年人世界的法则。
十分钟后,我从书房走出来。
安然已经不在了。
陈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背脊佝偻,像一瞬间老了十岁。
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那支笔。
他抬起头,看着我,声音嘶哑。
“我选B。”
我点了点头,意料之中的答案。
“好。”
我走到他面前,把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袋,放在他面前。
里面,是我刚才在书房中,迅速拟定的《婚姻忠诚补充条件》。
条条框框,逻辑清晰,权责分明。
比我处理过的任何一份商业合同,都更严谨。
“签吧。”
陈宴拿起那几页纸,他的手在抖。
他一页一页,看得极慢,极仔细。
他一读到那个最后一条,涉及“若再次违背承诺,须向双方亲属及企业决策机构郑重道歉”的内容,身体就猛地摇晃了一下。
他知道,这是诛心之策。
这彻底断了他所有的后路。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复杂。
有哀求,有屈辱,有不解。
“阿清,一定要这样吗?”
“是。”
我只回答了一个字。
克制不是恩赐,是义务。
同理,惩罚也不是报复,是规则。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反悔。
最后,他终究还是握住了笔杆,于契约的尾部,逐个描摹,落下了自己的署名。
陈宴。
那两个字,他写得格外用力,几乎要划破纸张。
我收起协议,一式两份,把其中一份递给他。
“收好。从这一刻起,我们的婚姻,进入2.0版本。”
“旧的规则已经作废,现在,我们按新的规则来。”
他没有接,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痛苦。
“阿清,我们之间,真的就只剩下这些了吗?”
“不然呢?”
我注视着他,语气平和地询问:陈宴,照明设备损坏了,我们能够安装一个崭新的部件。然而,安装该部件的整个建筑,倘若其根基都出现了不稳,你认为,是应当先商议部件的款式,还是应当优先处理建筑结构的问题?
“这些条款,就是我们婚姻新的地基。”
它缺乏暖意,甚至相当寒冷。然而,至少,它能够确保这处居所,在短时间内不会崩塌。
安然是哭着离开的。
陈宴送她到门口,两人没有说话。
我站在客厅,能看到他僵硬的背影。
门关上,他转过身,看着我。
“她……工作的事,能不能……”
“不能。”
我打断了他。
“合同第一条,断绝一切联系。包括工作。”
我给你三天期限,必须解决这个状况。你可以接受N+1的补偿方案,或者考虑其他解决办法,核心是我希望这个人彻底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不留任何痕迹。
“这是规则。”
他闭上眼,脸上是深深的疲惫。
“阿清,我累了。”
他说。
近些年,公司状况,项目进展,以及……孩子的教育,都让我感到无比沉重。
“我喘不过气来。”
和她相处,感觉十分自在。我无需考虑任何事,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如此坦白地剖析自己。
不是为了辩解,而是一种近乎耗尽所有力气的陈述。
我静静地听着。
心里那块坚硬的冰,似乎有了一丝裂缝。
“累,不是你出轨的理由。”
我说。
“我也累,陈宴。”
这三年为了怀孕,我究竟服用了多少种药物,注射了多少剂疫苗,接受了多少回检测,你真的清楚吗?
每次平躺于冰凉的手术床,每次有器械进入躯体,每次抱有期待却再次落空,那种心境,你是否感受过?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征途,我们每个人都是肩扛重担的旅人。累了可以呼喊,倦了可以稍作停顿,但绝不能选择放弃。
我的声音,始终是平的,没有起伏。
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砸在他的心上。
他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
他一向在我眼前,显得无比刚毅,如同我的依靠,然而此刻,他首次展露出难得的脆弱神态。
“对不起,阿清。”
他哽咽着说,“真的……对不起。”
这一次的道歉,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真诚。
我没有说“没关系”。
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永远不可能没关系。
我只是走过去,从他口袋里,拿出了他的手机。
当着他的面,我找到了“安然”的微信。
我没有看他们的聊天记录。
我不是善良,我是不喜欢脏。
我直接按下了“删除联系人”。
然后,是电话号码,拉黑。
所有与她有关的痕-迹,被我一点一点,清除干净。
做完这一切,我把手机还给他。
“行了。”我讲,“今后,你做你自己,我做我自己。我们还是我们,只是不再是往日的我们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家里安静得像一座空房子。
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却隔着一条无形的楚河汉界。
他开始严格遵守我们之间的“新规”。
每天准时回家,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放在我面前的桌上。
他的微信步数,每天都在公司和家两点一线。
他的工资卡,第二天就上交给了我。
他甚至主动在手机上开启了位置共享。
他做得很“好”,像一个努力想要及格的学生。
但我们之间,没有交流。
吃饭的时候,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
睡觉的时候,只有彼此清浅的呼吸声。
那份协议,像一道冰冷的墙,横亘在我们中间。
它保证了婚姻的结构不散,却也隔绝了所有的温度。
周五晚上,他加班回来,手里提着一个袋子。
他把袋子放在餐桌上,对我说了那一晚之后的第一句话。
“路过水果店,看到石榴不错,就买了点。”
我愣了一下。
我喜欢吃石榴,因为医生说,石榴多籽,寓意好。
早些时候,我总是亲手将它们取回,逐个逐个地剥去外皮,然后盛放在晶莹剔透的碗中,那色泽宛若璀璨的宝石。
然后我们一人一半,窝在沙发上看电影。
我走过去,打开袋子。
里面是四个又大又红的石榴,每一个都沉甸甸的。
我没有说话,只是拿出一个,走到水池边,开始剥。
他站在我身后,看着我。
阿清,他忽然说起话来,语气带着迟疑,安然,她当天提交了辞职申请。
我的手顿了一下。
“嗯。”
我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继续剥着石榴。
红色的汁水,溅到我的手上,像血。
“公司给了她N+2的补偿,她没要,只拿了自己该得的。”
“她说……她祝我们好。”
我把剥好的石榴籽,放进碗里。
满满一碗,晶莹剔透。
我转过身,把碗递给他。
“吃吧。”
他没有接。
他只是看着我,眼里的红血丝比那天晚上更重。
阿清,我明白,我确实不对,那些规定,我完全承认,你想怎样处置我,我都甘愿承受。
“但是,我们能不能……别这样了?”
“这个家,现在比冰窖还冷。我害怕。”
这是他第一次,说他害怕。
我看着他,这个我爱了八年的男人。
从大学校园里的白衬衫,到如今西装革履的陈总。
我见过他精神抖擞的模样,见过他熬夜工作的倦容,见过他成果达成时的欢欣。
却从没见过他如此……脆弱无助的样子。
心里那道裂缝,又扩大了一些。
陈宴,我告诉他,摔碎的瓷器即便拼合,痕迹依然存在,我们之间,也无法复原了。
他承认了,语气很迫切,表示自己并没有打算返回原处,只是希望对方,能够考虑一下,继续朝前探索。
如同你所言,我们已迈入数字纪元,即便……即便仅是伙伴关系,也应当彼此关怀,难道不是吗?
他看着我手里的那碗石榴,眼神里充满了渴望。
那不是对石榴的渴望,而是对一种“家”的氛围的渴望。
我沉默了。
过了很久,我把碗放在餐桌上,然后,分了一半到另一个小碗里。
我把其中一碗,推到他面前。
“吃吧。”我说,“很甜。”
他看着那碗石榴,愣住了。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拿起勺子,挖了一勺,放进嘴里。
他用力地咀嚼着,仿佛在品尝什么绝世美味。
我知道,这碗石榴,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它不是原谅。
它只是一种许可。
许可他,可以试着,把这个家的温度,一点一点,找回来。
那晚之后,家里的冰,开始有融化的迹象。
他不再完全按照规定行事,而是开始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他清楚记得要处理垃圾,会自觉去拖地,在我炖汤期间,常常守在旁边,替我递送物件。
我们开始有了一些简短的交流。
“今天公司楼下的桂花开了,很香。”
“嗯。”
“妈打电话来,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吃饭。”
“下周末吧。”
对话依旧简短,但不再是死寂。
像冬眠的土地,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他正在厨房里忙碌。
他在煮面。
西红柿鸡蛋面,是我最喜欢吃的。
以前我加班晚了,他总会给我煮一碗。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不算熟练的背影,有些恍惚。
他听到声音,回过头,看到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回来了?我试着煮个面,不知道味道对不对。”
锅里,热气腾腾。
金黄的鸡蛋,鲜红的番茄,翠绿的葱花,在汤里翻滚着。
那是一种久违的,充满了烟火气的温暖。
我忽然觉得,眼睛有点酸。
我走过去,从他手里接过锅铲。
“我来吧,你盐放多了。”
他没有坚持,只是乖乖地站在一旁出轨的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尝了尝汤,果然咸了。
我兑了点水,又加了些糖。
面煮好了,我盛了两碗。
我们坐在餐桌前,面对面,吃着面。
“怎么样?”他紧张地问。
“还行。”
我说,“比你第一次煮的好吃。”
他愣了一下,随即想起了什么,笑了。
那是我们大学时的事了。
他初次为我掌勺,做了一碗盐粒未溶,面条凝成一块的“爱心面”。
我一边吐槽,一边吃得精光。
那是我们,回不去的过去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怀念,有伤感,还有一丝小心翼翼的希冀。
“阿清,那块玉坠……我收起来了。”
我握着筷子的手,紧了一下。
那是他母亲给他的,说是陈家的传家宝,要给未来的孙子。
他一直贴身戴着。
“我把它,连同过去的我,一起锁进盒子里了。”
他说。
“我知道,我不配再戴着它。”
“等什么时候……你觉得我可以了,我再拿出来。”
我没有说话,只是低头,继续吃面。
汤很热,暖意顺着食道,一直流进胃里。
我忽然觉得,或许,他说的对。
我们应该往前走。
并非为了重温旧日时光,而是为了,迈向一个虽不可知,却可能充满希望的前程。
婚姻这份盟约,当其中一方违背了重要承诺,另一方有权决定终止关系,以此减少损失。
或者可以考虑,当面临严格的附加条件时,向对方提供一个“继续试用”的选项。
我选择了后者。
因为生活不是法庭,不是只有黑白对错。
它是灰色的,是复杂的,是充满了各种无奈和妥协的。
如同柑橘,纵然味道带刺,只要添足了甜料和液体,依然可以调制出味美可口的饮品。
我不知道我和陈宴,需要加多少糖,才能抵消掉那份背叛的酸涩。
但至少,我们都在努力。
日子,就在这种平静又克制的氛围里,一天天过去。
陈宴严格遵守着我们之间的协议。
他的生活,变得像一张透明的白纸,在我面前一览无余。
我们的关系,也在缓慢地回温。
虽然依旧分房睡,但他会在我睡前,给我送来一杯热牛奶。
我会在他出差前,默默地帮他把行李收拾好。
我们如同两个谨慎的伙伴,共同支撑着这个组织的日常运作,竭力确保其稳定发展。
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
那天是周末,我们一起回我父母家吃饭。
饭桌上,我妈又提起了孩子的事。
阿清啊,你们两个年龄也不小了,这件事得赶紧办妥。你父亲和我,都盼着能得个外孙呢。或者,要不要再去寻访那位声名显赫的老郎中?
陈宴的脸色,微微白了一下。
我握住我妈的手,笑了笑。
“妈,这事儿不急,顺其自然吧。”
实在让人不淡定!母亲嗓门陡然拔高,你已届三十二岁,倘若继续耽搁,便要当高龄生育者了!
陈宴悄悄地为我夹了根菜,小声说道:母亲,错在我,您不要责备阿清。
我妈愣住了,随即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回家的路上,车里很安静。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心里五味杂陈。
孩子,是我们之间,永远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也是压垮他,让他去外面寻找片刻喘息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到家,陈宴去洗澡。
我坐在沙发上,有些疲惫。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