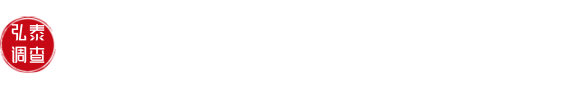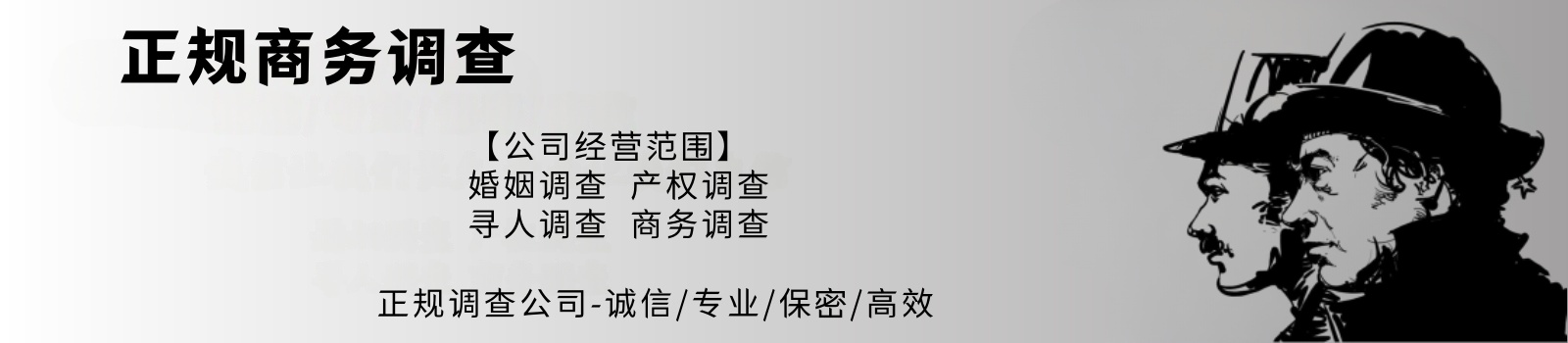- 手机:
- 13728687007
- 电话:
- 13728687007
- 邮箱:
- admin@youweb.com
- 地址:
- 广东省中山市
中国的口述实录写作起源于文学领域,后来在新闻界广泛传播,并在历史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写作方式与一般写作最大的区别在于,作者放弃了主导叙述的权力。大多数口述实录作品呈现出“众声汇合”或“碎片拼接”的特点,通过众多声音的相互补充和协调,从多个层次和角度生动地展现了真实世界的辽阔与复杂,真实地反映了民众的生活状况。在口述实录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每个人的回忆都有可能存在失真的风险;而且,作者对于叙述的放弃,并不完全如其所宣称的那般彻底。
关键词:口述实录/话语权/众声集纳/碎片化
自20世纪中期起,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口述实录,逐渐崭露头角。这种风格起源于美国史学研究,随后逐渐扩散至全球的史学、新闻以及文学界。我国首部口述实录作品问世于1985年,由作家张辛欣和桑晔共同创作,名为《北京人》。这部作品被评论界誉为“口述实录文学”。二十多年来,我国诸多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创作了大量具有深远影响的口述历史著作,这一现象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化景观。口述历史写作与一般写作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话语权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时代意义。它的诞生与成长,它的价值所在与局限性,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记言”作为一种关键的文学形式占据着重要地位。起初,这些被记录的“言”主要涉及君王的言论,随后逐渐扩展至史书中传主的话语,最终乃至普通百姓的言语。《礼记·玉藻》中记载:“天子一举一动,左史便记录下来;一语一辞,右史便记录下来。”而《汉志》中的描述则被视作对《礼记》的延续:“古代的君主世代设有史官,君主的一举一动必定被记录,这是为了谨慎言行,彰显法度。”左史记下言语,右史记述事件,事件被收录在《春秋》中,言语则被记录在《尚书》里,历代帝王都对这两种记载给予了认可。”尽管“左右”的记载存在差异,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都着重于如实记录君王的言行。在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将史传的写作形式归纳为四种类型,其中“记录言语”便是这四种类型之一,所记载的言语主要是史传中传主所发表的话语。明代时期,知名学者李贽在《焚书·答耿司寇》一文中提到:那些市井中的普通人,他们亲身从事自己的工作,口中谈论的也都是自己的事务。从事商业的人只谈论生意,务农的人只谈论耕作。他们的言辞朴实而充满韵味,确实是充满德行的言论,让人听了都不觉疲倦。他主张记录民众的“美德之语”,这体现了他对民间声音、个人声音的深厚情感,然而,鉴于封建时期文人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固有的隔阂,他想要深入倾听和记录民众心声的美好愿望并未完全实现。
尽管中国文人非常看重“记言”,然而在我国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中,“记言”并未形成一种独立且完善的文体。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言者”及其所发表的观点都是叙事中的被描述对象,作者对它们进行表述和评价,而“言者”本身并不处于主导位置;另一方面,所记录的内容多为言辞的片段,主要以作者所推崇的哲理之语、辩论之辞、机智之谈以及道德之言为主,只是零散的语句,无法形成连贯的言辞流。与那些早已存在的记言文体相较,当代口述实录在两个关键方面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讲述者亲自负责叙述故事,作者放弃了叙述的职责,仅扮演记录者的角色;其次,口述内容由连续的话语组成,本身具备一定的完整性。
20世纪40年代,口述实录在美国问世,起初仅作为收集历史资料的途径。1948年,尼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设了口述史料学的研究机构,随后在1960年,他推出了首部《口述史料汇编》。不久之后,若干新闻从业者与文学家手持录音设备,踏入社会,他们开始聆听民众的声音,并通过录音设备真实地记录这些话语。随后,他们从中挑选部分内容,将其转化为文字,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或集结成册出版。自此,口述历史记录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写作模式。
在美国,斯特兹·特克尔是极具影响力的口述实录作家。自1950年代起,他开始创作。到了196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街头进行录音采访。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口述实录作品——《断街——美国都市采风录》。这部作品以芝加哥市民为访谈对象,收录了70位美国人的谈话内容。特克尔有意挑选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民族背景、肤色、性别、年龄段、职业、收入水平、文化背景和政见的人进行访谈,却有意避开宗教、教育、新闻和写作领域的人士,理由是“他们日常已经说得够多了”。《断街》的成就让特克尔对口述历史记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0年情感口述实录,他推出了《酸辛岁月——美国经济大恐慌的口述实录》一书,书中收录了160位人士的访谈故事。随后在1972年,他出版了《工作》一作,该书集结了众多人的对话,从银行经理到街头小贩,各行各业的人物都有涉及,详尽地描绘了他们的生活艰辛与快乐。②特克尔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实录作品,则是1980年问世的《美国梦寻——100个美国人的100个美国梦》。此次采访的对象包括美国小姐、雇佣枪手、知名影星、著名歌手、政坛人物、企业老板、流浪汉、大学生、罪犯、虔诚教徒、三K党首领、城市中的邻里街坊、贫民窟中的年轻女子、山区的乡民以及移民及其子女等,他们代表了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正如标题所揭示,本作聚焦于“美国梦”这一主题,受访者在麦克风前尽情分享他们在美国的梦想以及追逐梦想的历程,总计100篇访谈。作者依据内容的差异,将这100篇访谈划分为多个类别,并在每个类别中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小组,每组包含一到数篇访谈。为了完成这部著作,特克尔总共采访了300位受访者,而书中的100篇访谈则是从这些采访中精心挑选而来。这部作品荣获普利策文学奖,因而被誉为全球公认的文学经典,极大地提升了特克尔的声望。
采用此方法的作家远不止特克尔一人,1970年,作家劳伦斯·桑德斯凭借《安德逊录音带》一书,将原始录音带中的语音转化为文字,成功出版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受到了著名作家阿瑟·黑利的赞誉,他评价道:“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小说形式……令人着迷,充满趣味,情节紧凑。”在欧洲,涌现出了若干部颇具影响力的口述实录作品,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德国作家玛克西·万德尔的《早安,美女》以及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的《战争中没有女性》等。
张辛欣在中国率先开展了口述实录的写作实践。1984年,她与桑晔共同商定,计划撰写百篇关于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为此她们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进行采访。次年,即1985年,《钟山》、《收获》、《文学家》、《上海文学》、《作家》这五家知名文学期刊的第一期,同步刊登了她们以《北京人》为总题的80余篇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在文学界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反响。随后,散文作家周同宾的口述实录作品《皇天后土——99个农民说人生》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而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与安顿的《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亦跻身畅销书榜单,标志着我国口述实录写作的崭新开端。
观察我国口述实录的形成与演进历程,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其起源自文学范畴,后在新闻界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历史学领域得到充分发展。然而,口述实录作为一种边缘的写作形式,其作品在学科分类上常常模糊不清,难以明确归属,因此对于上述观点的理解不宜过分固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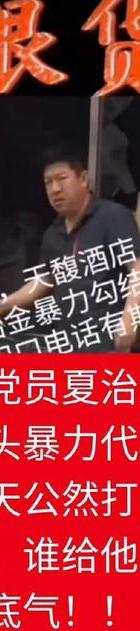
采访张辛欣时,有人指出,若非《北京人》一书的问世,我国口述实录文学的诞生或许会延后。这一观点无疑肯定了张辛欣与《北京人》在我国口述实录文学发展史上的先锋作用。“北京人”是对中国猿人的别称,在此处则代指中国人。张辛欣在挑选采访对象时显得深思熟虑,她邀请的嘉宾来自各行各业,性格各异:有喜谈“近两年生活改善”的山东农夫、有过偷尝禁果经历的回城青年、在酒吧漂泊的失业青年、守候公用电话的老妇人、传播“速算技巧”的街头智者、不走寻常路的美术院校学子……每位嘉宾都有独特的身份,也展现出不同的个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有意保留了对话的原始形态,将讲述者极具特色的言辞和语气完整地呈现于文中。这使得这些角色形象栩栩如生,仿佛跃然纸上,让人难以忘怀。
1986年,著名作家冯骥才在《今晚报》上发布了一则启事,目的是征集关于“文革”时期遭受苦难的经历。同年,他在该刊物上推出了《一百个人的十年》这一系列作品的初稿。为了撰写这部作品,冯骥才阅读了约四千封来信,并对数百名来自不同行业、见证“文革”的个体进行了采访。《一百个人的十年》历经多次出版筹备,终于在1997年10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一百”一词中山可靠侦探公司,寓意着整体概念,全书共收录29篇文章,详细描绘了数十位人士在“文革”时期的亲身经历。冯骥才指出,该书并非出自创作,而是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内容仅为对受访者叙述的忠实记录,其中不包含任何想象或虚构的元素。
周同宾,一位散文作家,他的口述实录著作《皇天后土》的创作起始于1980年代末。在作品集结成册之前,其中的内容已分批在众多文学期刊上呈现,累计超过百篇。最终,周同宾从这些文章中精选出99篇进行出版。这部作品的副标题为《99个农民说人生》,周同宾致力于让农民们直接表达自己的心声,呈现他们本真的生活状态。在此过程中,他仅担任记录和剪辑的角色,坚决不进行任何美化或修饰。采访与撰写工作极为不易,常常是十几人参与其中,却仅有寥寥数人能提供有价值的见解。④这一点充分表明,口述历史记录文学的创作过程亦如同从沙中淘金一般,“看似轻松实则充满艰辛”。
林白这位知名小说家在步入21世纪后,其创作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05年发表的《妇女闲聊录》便是这一转变的显著标志。这部被称作“长篇小说”的作品,与林白此前的作品风格迥异,同时也与一般小说的文本格式有着明显的区别。林白毅然决然地让一位乡村女子占据了她的位置,她主动放弃了作家应有的话语权,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语言的冲突:乡村的声音打破了文学论坛的和谐与秩序……⑤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的异质存在”。作家未曾发表任何观点,她仅是倾听者与记录者,几乎是逐字记录,使得讲述者的原始形象得以完整保留。该作品由超过两百个片段拼接而成,其中蕴含着世界整体性已被完全摧毁的寓意。因此,评论家们以“叙述的革命”这一术语,对这部极具胆识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四部作品均由文学家创作,在文体分类上,作者们的看法各异:林白将《妇女闲聊录》视为小说,周同宾将其归类为散文,冯骥才将自著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称作纪实文学,而张辛欣对《北京人》的文体归属并未明确表态,评论家们则将其誉为口述实录文学。这四部作品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当代口述实录文学的典范之作。
口述实录的写作在新闻领域相对较晚兴起。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不少报纸与杂志相继设立了口述实录的专栏。随后,一些网站也纷纷推出了此类专题页面。在这些早期进入并产生显著影响的作者中,有《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安顿。1997年,她在该报的“人在旅途”专版中开设了“口述实录”这一专栏,专门用于刊登以婚姻家庭为话题的深度访谈。翌年五月,安顿挑选了部分作品汇编成册,命名为《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该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成为当年备受瞩目的畅销书之一。此后,安顿还陆续推出了《回家》、《绝无禁忌》、《相逢陌生人》等众多作品。《北京晚报》设有“私密独白”这一栏目,该栏目的主持人郭晋丽分别在2000年和2003年推出了两部同名的书籍,书名均为《私密独白》。这些作品与安顿的《绝对隐私》在出版时间上相仿,内容话题也颇为相似。此外,还有一本名为《婚内婚外:情人、夫妻和第三者口述实录》的书籍,它也可被看作是“类新闻”体裁的作品。2006年,一位美籍华人女性作家黄梅子在中国大陆推出了她的作品《网络姻缘——跨国网络征婚口述实录》,这一举动显示出以婚姻和家庭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我国的持续发展态势。
相对而言,仅有少数几部作品在探讨生存意义时超越了婚恋议题,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度较高,因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较高评价。比如,2004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家庭》,该书真实记录了农民工在北京的打工与生活状况。此外,还有女作家于秀在更早时期出版的《遭遇下岗》等类似作品。
新闻阅读因其时效性而备受关注,尤其是报纸,常被学术界戏谑为“寿命仅一天的畅销读物”。尽管新闻领域拥有广阔的阵地和丰富的作品,然而,大多数作品却只是迎合了读者的时尚喜好,话题内容单一且相似,缺乏深度。某些所谓的新闻类图书专题亦面临相同困境,比如在2003年,多家出版社几乎同步发布了诸如《晨曦之后话别离》、《破晓时分情已散》、《晨曦之后情未散》等记录“一夜情”的口述回忆录,这些作品既缺少了文化历史的深厚底蕴,又未能深入挖掘时代精神,故而未能赢得读者的喜爱。
在历史研究领域,口述实录写作的进步显得既稳健又深刻。经过最初仅作为搜集史料手段的起步阶段,史学界对口述实录的应用已经转变为一种自觉的写作实践。中国大陆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最早可追溯至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所著的《胡适口述自传》。唐先生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委托,对胡适进行了采访,共进行了16次正式录音,从而完成了胡适的英文口述自传。这部作品最早于1986年由台岛传记文学社出版。随后,1993年情感口述实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简体字版本。此后,该书被多家出版社重新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21世纪起,我国开始大规模出版口述历史类著作。2002年,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张学良世纪传奇》,此书以唐德刚教授对张学良将军进行的十余次访谈录音为基础整理而成,作者署名为王书君,全书包含100章,内容丰富。然而,该书的部分版权和内容的真实性后来遭到了质疑,有消息称其并未获得唐德刚教授的授权。至2007年7月,唐德刚先生授权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由中国档案出版社正式发行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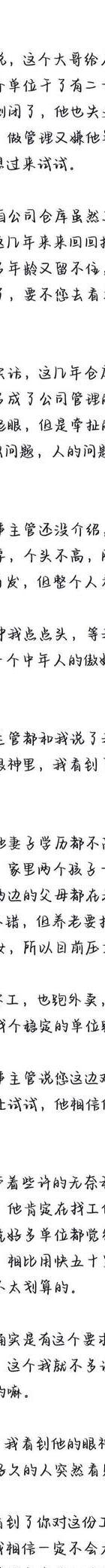
在2003年,我国知名的三联书店出版了两部颇具影响力的口述史作品。一部是由邢肃芝(洛桑珍珠)亲自口述,并由张健飞、杨念群进行笔录的《雪域求法记——一位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另一部则是女性研究领域的专家李小江主编的,共四册,总名为《让女人自己说话》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系列丛书。李小江的著作以女性视角为核心,剥夺了男性在话语上的主导地位,全书由女性亲自讲述她们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体验。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审视历史,开创了全新的历史解读视角。在《文化寻踪》一书中,作者聚焦于女性与历史文化的交融,探讨了婚俗、缠足以及“自梳女”等女性生活状况,同时涵盖了女性文学、景颇族的传统服饰、窗花剪纸等女性文化艺术领域。《亲历战争》一书从女性视角出发,揭示了战争中被忽视的历史片段。《民族叙事》则收录了少数民族妇女的口述故事,其视角尤为独特。《独立的历程》一书聚焦于教育与职业两大主题,详细记录了中国妇女百年来从家庭走向社会、实现解放和独立的过程。这套丛书凭借“口述”与“女性”这两个显著特点,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口述史的编辑和出版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自2003年起,他们陆续推出了“口述历史”与“口述自传”两大系列丛书。与此同时,他们还出版了探讨口述史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著作《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到了2004年1月,出版社又特别推出了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书中收录了13位知青关于他们上山下乡经历的口述记录。讲述者中既有当年的知青代表,又有民间的知青首领,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他们的家庭背景、人生观千差万别,在那次上山下乡的浪潮中,他们的经历各具特色。因此,他们对那段岁月的感受、理解和评价都带有浓厚的个人印记。他们的亲身叙述,相较于以往的知青历史著作和知青文学作品,显得更为详实、更为真实。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徐晓对口述实录情有独钟,她策划的《洗礼岁月——七七、七八大学生口述实录》以及《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告白》等作品,在选题上颇具匠心独运之处。
前面的列举大致勾勒出了口述实录写作在我国二十余年历程中的起始与进展情形,内容虽然不够详实,却也难免显得零散。
口述实录与一般写作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叙事权力的掌控者上,换言之,关键问题在于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在过去的写作中,尽管作者身份多样,各不相同,但总体来看,只有两类人掌握着话语权: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这种现象使得权力与知识往往相互依存,导致大多数人的声音被忽视或湮没,众多知晓真相的人沦为“沉默的旁观者”。即便某些作家自觉承担起代表民众发声的职责,这也仅仅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愿望。然而,实际上,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立场,这种立场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他们的思考,进而左右了他们的抉择、评价和言辞,同时也制约了他们构建和重现现实的能力。他们的声音永远无法等同于“他者”的声音。此外,我们还需明确“转述”与“实录”之间的差异。奈达尔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修辞、叙事技巧以及文风不仅对事实进行组织,更会对事实本身进行改造。他意在提醒我们,在写作过程中,语言、叙事和修辞均可能对事实进行扭曲、调整或修正。因此,“转述”与“记录”并非同一概念。值得庆幸的是,当代学者福科的“话语理论”为写作者敲响了警钟,促使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对自身掌握的话语权产生质疑与反思。恰逢此时,便携式录音设备的问世使得对原声的“真实记录”变得可行。因此,一些作家开始将自己从滔滔不绝的发言者角色转变为专注倾听的接收者,将话语的主导权让渡给了“他人”。历史学领域的口述记录,其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保留当事人最初的言辞,为传统历史文献提供对照。然而,新闻与文学领域的口述记录,却有着更为深远的追求。他们力求通过挖掘那些在以往任何文本中未曾出现的民间声音,来揭示民众眼中的真实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口述记录的兴起,标志着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话语权变革。斯特兹·特克尔在创作《断街》之际,刻意避开宗教、教育、新闻以及写作界的身影,其目的在于将话语权赋予那些沉默者。同样,我国作家周同宾在谈论《皇天后土》的创作初衷时,也表达出这种自觉性,他指出:“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多不愿为农民发声,不愿将偏远乡村的琐事和村民们的粗俗言语如实记录于文章之中。”陈胜与吴广若终其一生仅限于田间耕作,未曾高举义旗引发动乱,从而获得显著的名声情感口述实录,那么司马迁便不会在《史记》中记载他们的生平”,而如今,又有哪位享有盛誉的作家愿意深入偏远乡村,敲响农家的柴门呢?周同宾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让每一位农民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言论,讲述自己的身世、生活、人物、事件,表达感慨或牢骚,无论何种形式……虽然单个人的话语可能显得薄弱,但当众多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便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
除了少数如胡适、张学良等人的自传性口述史讲述具备一定的完整性,大多数口述实录作品多表现为“众声汇聚”或“片段拼凑”的形式,即便是归类于口述史领域的某些作品,例如“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亦是如此。《北京人》的副标题是“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而《皇天后土》则特意挑选了99篇中山哪里有正规的外遇调查公司,以避免显得过于完整。《妇女闲聊录》虽由一人讲述而成,但全书实则由200多个片段拼接而成,与传统叙事的“井然有序”大相径庭。这种结构形态的采用,实为口述实录作者们不谋而合的选择,可视为他们后现代意识的体现。后现代主义观点认为,世界的整体性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假象,而真实的世界实际上是由众多碎片拼接而成的。“宏大叙事”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完整性与清晰度看似无懈可击,实则令人质疑。这种叙事模式将世界简化为某些固定理念所定义的狭小空间,叙事者自诩为智者,认为自己掌握了是非曲直的最终评判权,试图用所谓的“真理”来教导读者。然而,实际上,他们却局限于一个自以为是、狭隘的思维框架之中。这种狭隘的视角,那种乏味的声响,对读者而言早已变得微不足道,成了无关紧要的陈词滥调,甚至是聒噪的噪音。而口述实录的汇编方式,一方面促进了民间声音的狂欢,另一方面则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世界的真实面貌。仅需在阅读过《北京人》与《皇天后土》两部作品后稍加思索,便会不由得认同,任何一部传统叙事的巨著,均无法像这两部作品一般,在众多声音的相互补充中,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生动地展现出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世界的广博与深邃。《妇女闲聊录》中所收录的个体声音,尽管如此,却因避开了僵化的秩序整合,成功呈现了真实的民生景象,让人不禁联想到庄子那句“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至理名言。
口述实录写作,无论是直接归属于历史范畴,还是融入新闻与文学的天地,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表述。在历史的广阔天地中,我们还能区分出“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差异。“大历史”往往忽略具体细节,着重于总结性的观点,它是一种经过特定意识形态整理、条理清晰的宏大叙事;相对地,“小历史”则是分散的、片段的、注重细节的个人叙述,并未被纳入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无论是“大历史”还是“小历史”,都受限于特定的语境进行解读,都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记录历史。任何一种解释都不等同于绝对真理,也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和永恒性,每个人都有权对自己所经历的时光进行个性化的描述。口述历史记录的写作,显然并不怀揣构建宏大历史的雄心,它所追求的,是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的细节,体现历史的真实面貌,让那些历来宏观的历史表述重新回到具体生活的根基之上。这种所谓的“小历史”越多,历史的内涵便愈发充实,而在“大历史”的叙述文本中,那些原本存在的缺陷,如不完整、模糊、含糊其辞以及矫揉造作,甚至是在权力压迫下产生的变形,便更有可能得到补充和纠正。
在此,我们已从理论角度对口述实录写作在现今社会出现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然而,我们亦需认识到,这种写作形式本身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警觉。
必须明确指出,口述实录中所收录的言辞,主要源自讲述者根据个人立场进行的回忆性叙述,而每个人的回忆都有可能出现偏差,无论其态度是否真挚。钱钟书先生,这位知名学者,曾提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回忆并不可靠,一个人在创作过程中所展现的想象力往往显得单薄且可怜,而到了回忆阶段,他的想象力却常常变得丰富且离奇,令人惊叹。过去数年,一些评论者提出了与钱钟书先生相近的看法:人们所铭记的,不过是自身生活领域中的一小部分经历与常识。记忆的这种选择性,使得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真相究竟为何一无所知。由此观之,任何回忆性质的文本,都无法成为记录历史真相的可靠依据,而仅仅是作者进行的一次想象中的语言探险。在众多学者的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些名人甚至伟人的回忆录中存在不少错误,这其中不乏有意或无意的自我粉饰。此外,普通民众在讲述个人经历时,往往难以避免地融入了个人立场带来的偏激情绪和不理智成分。在这些充满激情的言辞和看似合理的论证背后,往往隐藏着需要剔除的杂质。